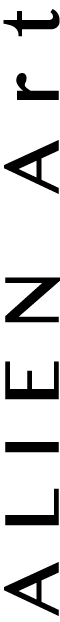
「能在具體實現意想不到的表現當中,找到最多激勵,而這個現象的最大意義或許就是所謂的『禪』。」-嶋本昭三
我研究嶋本昭三的作品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最初是因為一位多年朋友迪亞哥・斯特拉澤(Diego Strazzer)的緣故,他是收藏家,也是藝術製作人。感謝義大利那不勒斯嶋本昭三藝術協會的出色典藏,我才能在最好的條件下做研究,特瑞莎(Teresa Carnevale)與朱賽佩・莫拉(Giuseppe Morra)稟持對美學的熱情與科學的嚴謹態度,保存許多珍貴的作品與文件,使我們得以正確瞭解及欣賞嶋本昭三傳承的重要性。從阿曼(Arman)到蔡國強,再經過米羅(Miro),對於會著手處理「破壞式創作(Destructive Creation)」 之複雜與形而上問題的藝術家,向來都令我深感著迷;我曾在自己的《蔡國強與龐貝:進入火山內部(Cai Guo-Qiang and Pompei: inside the Volcano)》一書中討論過「破壞式創作」這個名詞。 毫無疑問的,破壞式創作一直是 20 世紀下半葉中,視覺藝術發展中的主要過程。在歐洲,我們立刻就會想到燃燒木板來創作的布里(Alberto Burri)、將畫布割破的封塔納(Lucio Fontana),或是燒掉自己 1970 年代最後畫作一部分的米羅(Miro)。 2005 年,龐畢度中心的總館長凱薩琳・格雷尼爾(Catherine Grenier)在巴黎現代藝術博物館策劃了「大爆炸: 20 世紀藝術中的破壞與創造」展,而在為了這個展覽完成的學術論文中,她甚至指出「 20 世紀與我們當代藝術家作品的共同起源,就是 [...] 一個串連「破壞」與「創造」這兩個名詞的自相矛盾衝動(Paradoxical Impulse)。」在我看來,對於這個「自相矛盾的衝動」,可以想到許多原因。首先有一種比我們的時代更久遠的美學與古典作法:十八世紀的法國哲學家與藝術評論家狄德羅(Diderot) 已解釋過破壞如何具備創造性,並反駁了創造與破壞是兩相對立的普遍看法。在他的傳奇性論文《沙龍評論(Salons)》中,狄德羅(Diderot)就想像,若法爾孔奈(Falconet)的畢馬龍雕像能就地破壞,將會變得更完美......之後,在一首代表近代開始的 19 世紀末詩作中,詩人韓波(Arthur Rimbaud) 也在他的《彩畫集(Illuminations)》 提出疑問:「我們能讚美破壞嗎?」在韓波的詩中,(古老)世界的特定破壞是新生命到來的必要序曲:「死神吹著口哨,沉悶的音樂盤旋,讓這個備受崇敬的軀體昇華,如同幽靈般擴大與顫抖;鮮紅及黑色的傷口在他們美好的肉體上綻裂開來。在這個混沌的地方,生命的潔淨色彩變得深沉並圍繞著這個景象起舞與浮現.....」:在《彩畫集(Illuminations)》裡,韓波(Arthur Rimbaud)希望能以詩(亦即藝術)「轉變」生命;在這當中,只有經過破壞,創作才能成為真實。為什麼災難能變成藝術創造的源頭呢?在二十世紀中葉的藝術中,這個破壞過程的極重要動機之一,絕對就是現代藝術家想擺脫古老世界的渴望,意謂著讓自己從學院派藝術的神聖規則中解放,並且擺脫創造「美麗」作品的責任。讓我們回想一下,在米羅(Miro)藝術生涯的早期,他說過自己的明確目標是希望「謀殺畫作」,亦即將他的藝術從學院藝術與規則中解放出來。畢卡索(Picasso)也重申:「我才不關心美。」最後而且同樣重要地,或許還有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為這個過程加入了恐懼與破壞:藝術家打算如何從一個被破壞的世界中,喚起創造的形式,進而恢復生命的意義?在布里(Alberto Burri) 2015 年於紐約古根漢美術館舉行的無與倫比回顧展中,展覽刻意地命名為「畫中的創傷(The Trauma of painting)」,在展覽一開始就是典藏照片的放映,展示在 1945 年徹底遭受破壞的義大利城市。如同博物館在其展覽介紹中的說明,這個展覽希望明確強調:「布里(Alberto Burri)的作品既毀壞也重新配置了西方的繪畫傳統,同時為代主義拼貼重新賦予概念。」事實上,透過在藝術中的發明創造,布里(Alberto Burri)在一個殘破國家的悲慘脈絡中,打造出一個新世界、一種新藝術。阿曼(Arman)也是在戰爭中長大,而事實上,其作品非常重要的一個面向就是以破壞式創造的過程為基礎。在他稱為「憤怒(Rages)」的表演中,阿曼(Arman)摧毀、打破、燒毀傢俱及物品,藉以「在破壞之中運用他的能量」,並從這個轉換式破壞的操作中創造全新元素。他將破壞後的碎片收集起來放在畫布上,製造出類似爆炸照片的構圖,變成了藝術作品,如同他在 1962 年 3 月一次破壞鋼琴的表演中所創造的油畫板《蕭邦的滑鐵盧(Chopin's Waterloo)》。在這個相同的歷史時期,且極有可能對上述這些歐洲實驗創作與藝術家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嶋本昭三在飽受戰爭與兩顆原子彈摧毀的日本,發展出他自己的「洞(Holes)」系列作品,並且燒掉與割破畫作。之後他透過「原子式(Atomic)」表演創造出全新的藝術形式;在表演中,他會在畫布上砸碎與爆破顏料瓶。在他最早的一個藝術行動中,在 1956 年蘆屋河岸的戶外具體派展上,嶋本昭三使用大砲將裝滿顏料的玻璃瓶射向一面懸掛在樹上的大型畫布上。在他的藝術生涯期間,透過將多色顏料瓶在畫布上爆開,將一層又一層厚物質砸在畫布上,以及在畫紙上打洞,進而催生出他的「洞(Ana)」系列作品,嶋本昭三一直在探索及拓展繪畫的疆界。透過突破一張一張黏在一起的報紙,嶋本昭三將他的繪畫想像為一個洞。
藉著嶋本昭三,藝術在象徵暴力與破壞的表演中再次重生。再一次的,藝術說明生命與美的形式能如何從混亂無序中誕生。從人類學的方法來看,會認為這個藝術過程或許具備一種淨化作用。對於二次大戰後的藝術家而言,藝術的責任無疑是要尋找生命的全新意義,並參與提出一個建立在舊世界殘垣瓦礫上的新世界。當「具體藝術協會(Gutai Bijutsu Kyokai)」(即之後為人熟知的「具體派」)在 1954 年創立時,就明顯表示戰後的日本藝術家必須將藝術場景徹底重置。連同畫家吉原治良(Jiro Yoshihara),嶋本昭三也是創立具體派的成員之一,且最終是由他提出「具體(Gutai)」一詞,而這個名詞在日文裡同時代表著「具體」與「體現」的意思:是一種表示藝術過程、具體行動及藝術家身體重要性的方法,以正確評價及瞭解藝術作品。參與具體派運動的藝術家都擁有共同興趣,而且都優先考慮藝術創作的過程,而非完成後的作品。這群年輕藝術家想要徹底地重新思考日本的藝術傳統,不僅參考了非正規作法,而且迫使他們走向「廢除」與「消滅」的方向。觀眾的反應讓人很難熬,嶋本昭三回想起當時:「那段時間對我們來說很悲慘,因為戰爭才剛結束,而我們是戰敗國,所以人們不想看見破壞與暴力,也不想接受自己做過的行為,所以我們所做的一切完全遭到觀眾漠視。」 具體派因此和西方的前衛藝術建立起關係,結果在很多情況下,變成多年後許多歐洲與美國藝術家所進行實驗藝術的先驅。從這點來看,嶋本昭三的例子就很具代表性,因為他是率先在五零年代以其他事物之名、以繪畫活動的名義「背叛」繪畫的藝術家之一。例如:早在「表演視覺藝術」的趨勢於 1960-1970 年代受到重視之前,嶋本昭三就藉著激流派(Fluxus)運動創造出一個所謂的創作藝術新形式,以及一個關於何謂藝術作品的新觀點。正如他說過:「繪畫的行為是要啟發自由的表達,這才是一位藝術家的真正作品」。即使藝術史學家正逐漸認清嶋本昭三的貢獻對二十世紀藝術的重要性,在宣揚及研究他時,依然必須將他視為產生至今最偉大與重要傳承的領導者。現在有許多藝術家都在追隨破壞式創造的美學以及由嶋本昭三開始的「表演式繪畫」,蔡國強很明顯就是其中一個主要人物,他在義大利那不勒斯拿坡里國立考古博物館(MANN)的最新展覽就是由我策展。透過他的代表性火藥畫作,蔡國強對著已成為傳統及理論的概念式現代藝術的標準開火,並在這個意義上藉著實驗重生為最大的藝術挑戰。一個涉及處理形式之創造的過程,是從破壞形式所開始。
目前這份關於在高雄永添藝術 ‧ 金馬賓館當代美術館展出之嶋本昭三畫作的概論,是和拿坡里嶋本昭三藝術協會及那不勒斯莫拉基金會一起合作進行,後者以收藏全球最多的嶋本昭三作品為特色。台灣是與日本有著深厚歷史文化交流的國家,而這個展覽代表了台灣前所未有的第一個嶋本昭三研究概論。我們的展覽共包含數種不同類型的作品,主要在展現嶋本昭三藝術的變化進展與過程,集大成的階段是他最後於義大利完成由那不勒斯莫拉基金會策劃的最壯觀表演,而那不勒斯莫拉基金會是致力於表演視覺藝術的開創性專門藝術中心。嶋本昭三的作品是帶有想超越形式、將表面視為一個客觀事實,以及將圖畫行動當成一個活動等明顯意圖的作品,萃取出超越物質作品的行動重要性,而某種程度上變得純粹的活動規模,就這個意義而言,除了活動本身,已變得和最終成果無關。這個計畫的核心反映出這個決定性的過程,並包含願意克服邏輯必要性,將超大畫布切割割成在之後更好運用,而且更容易在畫布上伸展的小片段(嶋本昭三在許多擲瓶藝術表演中都曾使用過)。對於這個特別的表演,此嘗試是為了重現最初發想的那個傑作、將大型黑白畫布上的多樣分散片段聚在一起,並讓觀眾能有概念,想像出嶋本昭三原本企圖達成的大小與規模。這個展覽也展出幾個罕見的畫作,一開始先是美麗且少有人認識的《Nyotaku》系列,接著是最知名的《Monochroms》系列,以及來自具體派領袖之傳奇公開表演的擲瓶藝術畫作。最後還會展出一個關於影片的作品,是一個能讓人預見美國前衛藝術的特別體驗。在這個七分鐘的影片中,可以看見 50 多歲的嶋本昭三正在親手處理影片,他為黑影照片加上顏色,甚至是擺弄影片直到部分影片斷裂。這些特色之所以讓這個影片變成極特別的作品,在於它是數年後一些開始手動修改影片之西方實驗電影大師的先驅。我們也會播放嶋本昭三的義大利現場表演影片,在影片中,可以觀賞傳奇的「擲瓶畫作」系列的創作過程。他在 2008 年於總督宮的表演標題是:「Samurai acribata dello sguardo」,意思是「視覺特效的日本武士」… 確實是全力以赴運用色彩的日本武士,為了讓我們看見與想像這個藝術手法的精髓:亦即對自由的讚頌。在一篇知名的文章《你必須畫得不好》,嶋本昭三主張:「若要讓人感覺自在,就必須設定『別畫得好』的條件,而這正是繪畫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此就能讓我們回歸原點,也就是繪畫的喜悅,而非對技巧的考驗。」在這個刻意挑釁的宣言中(他曾說過:「藝術是要讓人驚愕的東西」),嶋本昭三想證明精湛技藝與學院藝術的約束及限制規定無法造就出新的藝術形式,相反地,「透過持續地畫得不好(嶋本昭三意指繪畫時要跳脫學院藝術的規範與規定),才真正有可能創造出醜陋、個人化與獨一無二的風格。最有趣的新藝術正是如此才得以存在,而創造也是於此開始。」
我們的展覽目的是要透過嶋本昭三的精選作品,展示新風格如何從這個美學宣言中浮現的過程,這是在隨後啟發全球各地許多當代藝術家的前導作風。別忘了,嶋本昭三的作品已在全球各地廣泛地展出,在 1993 年、 1999 年與 2003 年,嶋本昭三都正式受邀參加藝術節主要指標的威尼斯雙年展。在 1998 年洛杉磯當代藝術美術館策展的「出於行動:在表演與物體之間, 1949 - 1979 年」巡迴展中,他的畫作是和封塔納(Fontana)與波拉克(Jackson Pollock)的作品並列一起展示。 2014 年,紐約古根漢美術館在「具體派:燦爛的遊樂園」特展中,展出了幾件作品。在近期的 2018 年,義大利知名藝術史學家阿基里・博尼圖・奧利瓦(Aquile Bonito Oliva)在前衛的歐洲宣言展中,於巴勒莫策劃了一個迷人的回顧展。如同多數後二次大戰世代的藝術家,嶋本昭三向來都是和平行動主義者。他有一個名為「和平的證明(Heiwa no Akashi – 2000)」的表演畫作,在這個作品裡,他將顏料罐扔到掛在半空中的水泥畫板,這個作品現在設置在新西宮遊艇碼頭的紀念碑。在日本繼續維持和平的前提之下,這個表演作品將會持續 100 年。
上文節錄自展覽出版《嶋本昭三:跨越藝術邊界》,本展覽由永添藝術(ALIEN Art)、義大利那不勒斯莫拉基金會(Foundazione Morra)與嶋本昭三藝術協會(Shozo Shimamoto Association)聯合舉辦,並由永添藝術執行長邵雅曼與前巴黎大皇宮執行顧問哲羅姆.努泰博士共同策劃。感謝義大利莫拉基金會(Foundazione Morra)創辦人朱賽佩・莫拉(Giuseppe Morra)與特瑞莎(Teresa Carnevale),以及迪亞哥・斯特拉澤(Diego Strazzer)。
WHIRLPOOL, 1967, 93x118 cm. Private collection
Punta Campanella 46 2008, 189x202 cm. Private collection
Capri 36, 2008, 202x213 cm. Private collection
Magi S, 2008, 150x200cm. Private collection
Shozo Shimamoto Palazzo Ducale Genova 2008 © A. Mardegan
Genova 23, 2008, 170x194,5cm. Private collection
Genova 36, 2008, 187x247cm. Private collection
Reggio Emilia, 2011, 167x200cm. Private collection
Kono ue o aruite kudasai (Please walk on Top, painted wood, installation view The Outdoor Gutai Art Exhibition 1956© Associazione Shozo Shimamoto
Painting with glass bottles of paint, the 2nd Gutai Art Exhibition , Ohara Hall Tokyo October 1956 © Associazione Shozo Shimamoto
II gutai Exibition Hurling colors 1956 © Associazione Shozo Shimamoto
Shozo Shimamoto Un'arma per la Pace piazza Dante Napoli 2006 foto di Fabio Donato ©Fondazione Morra

WHIRLPOOL, 1967, 93x118 cm. Private collection

Punta Campanella 46 2008, 189x202 cm. Private collection

Capri 36, 2008, 202x213 cm. Private collection

Magi S, 2008, 150x200cm. Private collection

Shozo Shimamoto Palazzo Ducale Genova 2008 © A. Mardegan

Genova 23, 2008, 170x194,5cm. Private collection

Genova 36, 2008, 187x247cm. Private collection

Reggio Emilia, 2011, 167x200cm. Private collection

Kono ue o aruite kudasai (Please walk on Top, painted wood, installation view The Outdoor Gutai Art Exhibition 1956© Associazione Shozo Shimamoto

Painting with glass bottles of paint, the 2nd Gutai Art Exhibition , Ohara Hall Tokyo October 1956 © Associazione Shozo Shimamoto

II gutai Exibition Hurling colors 1956 © Associazione Shozo Shimamoto

Shozo Shimamoto Un'arma per la Pace piazza Dante Napoli 2006 foto di Fabio Donato ©Fondazione Mor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