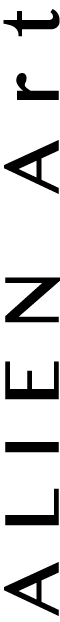
心向隱形鎌田治朗珠寶的創作哲思
隱形是時尚的終極目標嗎?確實,讓時尚之物保持曝光、無死角地接受觀察審視,是這個時代的特有負擔,卻也讓人產生消失自任何凝視的矛盾慾望。有人可能更願意離開妝扮自己的嬉鬧人生,進入暫時或永恆的隱形。
但實現隱形的機率又如何?物理學家相當懷疑。他們堅持,如果魔藥就能讓整個身體消失,就像H.G.威爾斯的隱形人裡寫的一樣,那至少雙眼還是會被看見的,不然光線根本進不了視網膜裡,結果就是自己也什麼都看不見。因此完美隱形的本身也包含外部世界的隱形。
其系列作品《Ghost》精準地傳達了這種試圖隱形的字句,但也發現一種無須遮蔽世界就能實現的隱形。觀眾達成一種比僅僅隱藏更強的隱形–即在鏡中觀察自己,而非觀察他人他物。然而最大的隱形的達成並不是觀眾的自我觀察,而是觀察的行為,比如幽靈這種東西。扭曲視野後再由雙眼視覺放大,作品密集呈現出觀察行為的現實。兩眼所見不可知也不可識。這種觀察行為並未停止,並要求我們放棄所有實際看到的一切。然而並不可能,於是被捲入美感暈眩。
這種純粹觀察的強烈體驗有種哲學的特性–也是鎌田治朗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深度反思部分。人要面對所有觀察和感知的基本條件,背景在此變成前景,哲學凝視只會是哲學凝視。
哲學一直是處理驚訝現象的方法。在作品《Momentopia》中,化身為珠寶的舊鏡頭本身就相當驚人。鏡頭不只是工業時代技術飛躍的象徵,同時也是最像人眼的東西。期望的是最大的透明度和可見度,然而實際遇到的卻是深淵。將最高透明度化為絕對影型的改造,擁有光特性的驚人晦暗令人憂心,因為所有可見之物的虛幻本質都被揭開了。同時,尼采的觀察當然也適合這裡:「當你凝視深淵,深淵也在凝視你。」隱形的代價是揭開自己內心的深淵。
純粹的光會因為觀測行為而產生分割。因此,由於部分失明的特性,雙眼才能以虛幻的方式看見事物。在這個情況下,只能透過差異與偏見、忽視與壓抑構成看見的畫面,盲目的狀態意味著所有觀看的原始條件。人會在這種條件下進入失明狀態,比如戀愛中的人們就是如此。戀愛中的人看事情都帶著一種奇特的美感,因為只讓心愛的通過,同時擋下其他的一切 (即反射)。這種情況也能看見BI系列。觀察者所注意到的是觀看中致盲行為的剩餘;只有剩餘部分,即是反相色,跟看到的顏色一樣引人注目。鎌田治朗的作品都用到了分色濾鏡或 鏡子,這種感知現象的透視時刻越來越明顯了。
這種包容排斥、看見與失明之間的複雜交互作用引發一種問題:我們想怎麼看?又想怎麼被看見?在今日霸道的極端曝光主義中維持隱藏狀態又代表什麼意思?這些被藝術家掀起的問題,好處在能穿上身,想得偏激一點的話,這些就是珠寶了。在這種戲劇性的時刻,提問轉為激問。就像帶著尖銳問題走過一群人,打破人群的完美沉默,如同雅典的第一位哲學家。藝術與哲學,是否為了一次又一次的掩飾且激發新的樣貌,誕生於提問轉為激問之處?
黑夜豔陽 兩種視角下的藝術系列《Flare》和《Mother》
沙漠
鎌田治朗經常說《Flare》系列跟他在阿他加馬沙漠中神祕的光線體驗有關。但對我來說,這片豔陽旱漠的畫面,反而給我阻擋他完成創作的怪異印象。作品Flare中超級顯眼的金色光球,相當偏離現實,無法想像是地球上真實出現的天氣現象。在鎌田作品中,以終極美感與完美型態導出抽象,讓具體體驗與作品的物性從此脫鉤。
然而當我看到他新系列的作品《Mother》時,沙漠的解釋便清楚表明了這點。只有繪出深邃的黑暗,才能清楚看到光面上謎樣光象的實際意旨。《Flare》中的眾多太陽將陽光密封在自己內部,甚至不允許一丁點 光線的洩漏,便能看作白天與黑夜間或母子間的大條分界,甚至是世界與逃離所謂世界的區別。這種遭遇確實存在,不過僅存於沙漠中。
一個相當有觸覺的想法
大理石在異教徒的廟裡輝映著太陽神的軌跡;奉獻的祭台充滿光明喜悅,體現在全知全能的不動之眼上。就像看見藝術家作業中的祭司之手,受到太陽的感召,不,是太陽的純粹思緒,繪出最純樸的式樣,作為裝飾物的純粹想法擁有矛盾的觸覺特性,也就是不可觸摸的形式。
《Flare》系列中最初的謎,是一連串太陽的形象。就像位在一顆夢幻星球的地平線上,我們被不只一顆甚至是三顆五顆十八顆太陽緊緊盯住。這種想法不會在分裂中失去純粹性嗎?確實能在這種變化中感受到清晰度的怪異上升;三顆或五顆的星座中,月球是最先被納入的。再往上加乘,原始想法納入了恆星。任何發出光、任何有能力撕毀夜晚面紗的事物,都完全被抽象的光所捕捉。
如此一來,我們就能繼續面對創作後面的謎–也就是鎌田的太陽實際上不具發光意義的原因。在《Flare Black》中,即使是背景也全然無光。黑夜之興的浪漫 主義有助於這種想法:光是沒有更原始黑暗就不會出現光。因此不可侵犯的柏拉圖思想,指向所有可見物的行程基礎夜晚。
黑夜是母親
發出再次見到孩子的欣喜–又或是淚水滿盈、乳白光芒的久別之悲?顯然,以陰鬱為標籤的形象,當星星 藏住黑夜的同時也藏住了光–明顯可見得只剩黑暗。深不可測的深邃在後開啟,使我們不能明視,並將我們帶到所有人的起源:史前歷史。仔細檢查之後,外貌卻是破損、零碎而不完整。因此這種深邃相當脆弱。同時卻也默許自己以無限的努力維持能。這面靈魂的半面明鏡,又是誰的母親?這個遠古以來最親密的親屬,是不是從未認識過?
把黑夜當母親的想法是舊的。黑夜一直是賦予生命的原始力量–孕育的顏色,但也決定死亡。我們知道有種來自基督教的變體,也就是黑色瑪丹娜的形象。從她黑暗的中心也生出了上帝,從而誕生光明世界,這是異界家園唯一的珍珠。鎌田的作品Mother,其模仿明夜的珍珠母也與這種傳統思想有關。這種人為的黑暗主要捕捉光出現的那刻,即短暫誕生的瞬間。大霹靂發生時,黑暗的表面各自分裂,光芒於斯誕生。
但是把《Mother》放在胸前,實際上帶的又是我們自己,是什麼意思呢?想一堆暱稱,盡力攀上關係,又是什麼意思呢?能變成我們的珠寶嗎?情況的轉換讓我們更顯得不值,從而教我們一種能強化自己的態度。即她比我們能表達的多更多,我們發現自己就像她所含的意義,戴著的同時也帶著我們自己。
"Sunrise in Atacama dessert" by Chile, 2013, © Jiro Kamata
Flare, 2016 © Jiro Kamata
Flare Black, 2017 © Jiro Kamata
Mother,2018 © Jiro Kamata
Ghost, 2016-17 © Jiro Kamata
Momentopia, 2008-10 © Jiro Kamata

"Sunrise in Atacama dessert" by Chile, 2013, © Jiro Kamata

Flare, 2016 © Jiro Kamata

Flare Black, 2017 © Jiro Kamata

Mother,2018 © Jiro Kamata

Ghost, 2016-17 © Jiro Kamata

Momentopia, 2008-10 © Jiro Kamata